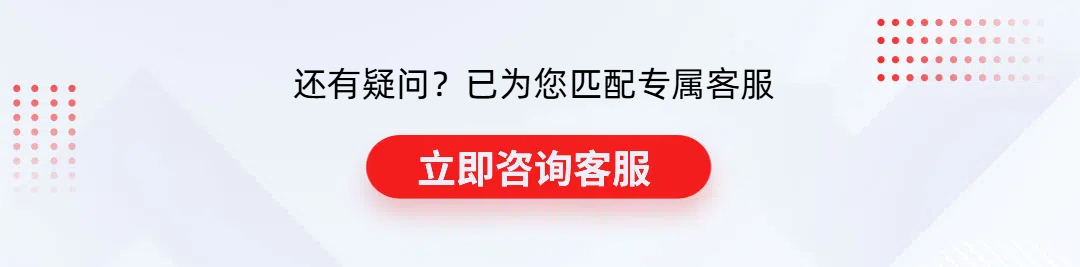1.0文化建构下的情爱追求
《长恨歌》译本中的王琦瑶在事业上以“沪上淑媛”、“上海小姐”等头衔得到了认可,满足了其虚荣心;生活上,与几位男性的情爱经历向广大读者诉说着她是一位积极并独立追求情爱的现代女性。
王琦瑶认定恩义是苦难,情爱才是快活,饱含着对自由情爱的渴望。
面对风流多情的老克腊,悬殊的身份与年龄已不再成为问题的焦点。
十八九岁的王琦瑶选择做李主任情人,被供养在华而不实的“爱丽丝”公寓,虽然他并不经常回公寓陪伴她,她却仍享受着这种保持性爱的关系。
原文:她和李主任的缘,大约就是等人的缘,从开始起,就是等,接下来,还是等,等的日子比不等的多,以等为主的。
(王安忆,1995:117)
译本:ShefeltresignedtohavingalwaystowaitforDirectorLi.Ithadbeenagameofwaitingfromtheoutset-thedaysshewaitedfaroutnumberedtheirdaystogether.(Wang2008:130)
原文中王琦瑶向命运低头,自入住“爱丽丝”公寓,便接受了男尊女卑的定义,一再妥协等待李主任,长此以往造成两性之间更大的差别。
生长在父权社会下的李主任有很强的优越感,当进入男女性别混合目标动力群体时,李主任的地位期望值远高于王琦瑶,自然将她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情人。
王琦瑶之所以被贴上女性这一社会性别的标签是因为在父权社会中的文化建构的影响下不得已而为之行为,李主任将王琦瑶视为他者,不停地通过各种行为方式巩固自己的存在。
译本中,王琦瑶认为等待只是一场游戏,在“爱丽丝”公寓里面唯一的活动便是打游戏。
既然是游戏又何须认真,游戏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娱乐,何必计较输赢。
译者使用“game”一词表现出不愿被动苦等的王琦瑶形象,她的心理活动被抽象化能使文章的情节引人入胜,她将好似无聊的等待看成是激情娱乐的游戏,试图从与李主任之间的男女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中抽离出来,在这场性爱游戏中,王琦瑶是一位积极的等待者,享受所发生的一切。
2.0母性情怀建构母女联盟
很多女性因为成为母亲,尤其是失去丈夫的母亲而在精神上对子女极度地依赖,并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黄立,2004)王琦瑶一生未嫁,却有个女儿薇薇,她希望通过母亲这一角色重寻女性的人生价值。
王琦瑶与薇薇的情感虽没有帮她树立为传统意义上的良母形象,但她以亲身经历教育薇薇女性应该自立自强。
薇薇的诞生是王琦瑶寻求自我价值的重要前提,她试图在以后的日子中与薇薇通过相互关爱与扶持建立密切联系,结成可靠的女性联盟并加以壮大,祈祷强大的女性群体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挣脱肉体与精神的桎梏,从而摆脱女性失语的现状。
原文:她忽然之间有些糊涂,想这孩子为什么就要没了?(王安忆,1995:215)
译本:Inherconfusion,shesuddenlybegantowonderwhatitwasthatdictatedthatthischildberemovedfromtheworld.(Wang2008:231)
原文中,王琦瑶是不明事理的准妈妈,对事情的认识模糊混乱。
在因循守旧的年代,王琦瑶犹豫是否要打掉腹中的孩子却不能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她之所以犹豫,不是因为女性与生俱来繁衍后代的职责,而是她所处的窘境——自古以来,女性想要成为母亲,必须建立在孩子和男人的基础上,否则必然会遭受流言蜚语。
原文中王琦瑶的犹豫是对掌控自己命运的犹豫。
译本中,译者的用词强化了王琦瑶应该将孩子生下来的信念。
dictate一词意思有totellsbwhattodo,especiallyinanannoyingway;tocontrolorinfluencehowsthhappens等,(霍恩比,2004)dictate与child类连接有悖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况且腹中的孩子是上帝意外的恩赐,王琦瑶的疑虑显然是多余。
译本中只提到她去医院检查身体并非原文中的去医院做手术,也再次肯定了她想留下这个孩子的愿望。
王琦瑶通过扮演未婚母亲的角色,摆脱了对男人的依附获得了相对的独立。
3.0宽广独立的人格魅力
王琦瑶用独有的魅力演绎着长恨与长爱,即使在寻觅美好爱情、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屡次受挫也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
她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顾朋友好言相劝毅然走入片厂;为了享受情爱生活,明知和李主任没有结局依然成为了笼中的“金丝鸟”;为了帮助康明逊,对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置若罔闻,甚至嫁祸萨沙。
王琦瑶没有埋怨过任何人,仍以自己的方式言说着女性的价值,具备比男性更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精神内涵。
原文:不过,原先的爱不欲生和痛不欲生也释淡了。
(王安忆,1995:245)
译本:Howeverthepassiontheyoncehadwasnothingincomparisontowhatitusedtobe.(Wang2008:266)
原文中,康明逊和王琦瑶过去的一段情是爱不欲生和痛不欲生,但后来心里的爱与痛都已释淡,以前要死要活的爱和痛全被时间烧成灰烬,强调了情感中的爱与恨。
译本里,王琦瑶过往的爱与痛用了passion一词来表达,passion有averystrongfeelingoflove,hatred,anger,enthusiasm,etc.之意。
(霍恩比,2004)若要表示负面的情感,通常会加上限定修饰词,如:violentpassions或acrimeofpassion。
译者将这种负面情感弱化和模糊化,留给读者遐想的空间,使读者忘却他们情感中的矛盾,挣扎,无助及焦虑。
性别是述行的,是由话语来制造的,那么王琦瑶的社会性别就并非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在康明逊的映衬下,王琦瑶俨然是雌雄同体,综合了男性的宽广心胸与女性的传宗接代等特质。
具备现代女性主义意识的王琦瑶试图颠覆传统女性主义的特质,不计前嫌地重新与康明逊的交往表现出了新时代的王琦瑶宽广独立的胸襟。
4.0王琦瑶形象美国化的原因
译者对王琦瑶形象的改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
译者曾在西方社会受过文化熏陶,中国女性形象在不同的中西方文化影响下甚有差异。
在中国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坏中,女性有生命无历史。
那里有妻子、有夫后、有妇人、有婢妾,而没有女性。
(孟悦、戴锦华,2004)这些女性的代名词都是依附于男人而存在,变成了他者。
“五四时代”是弑父时代,无论是黄淑仪因爱情而来的人生怀疑备受煎熬,成为怯者还是冯阮君笔下的女性对待爱情忠贞不渝,成为封建社会的反叛者,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新女性在社会与历史纵横交错下都有着过不去的坎,只有遵守“三从四德”的女性便能顶着“贤良淑德”、“良家妇女”的美誉。
而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女人应该是“聪明、健康、独立,并且以做一个中国人而无比的骄傲。”(伯瑞克·萨迪,2002)这样的女性形象远比传统的女性形象被西方人所熟知和爱戴。
由于文化差异,西方人对沉淀了数千年的传统女性文化意识的认识肯定带有局限性。
结语
《长恨歌》因其是女性作家王安忆所写才显得别具一格,王琦瑶独特的现代女性魅力在男性作家的笔下是体会不到的。
王琦瑶的一生都在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译本中译者并没有消除中西方文化差异背景,而是尊重隔阂,将美国元素填充于王琦瑶的形象,使其成为一位有思想,敢于挑战命运的现代女性,最终她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但在奋斗的过程中她无怨也无悔。
译本体现了译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适当的改写能够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避免文化碰撞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有效促进文学翻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Wang,A.TheSongofEverlastingSorrow:ANovelofShanghai[M].MichaelB.SusanC.E.(tran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8.
2.伯瑞克•萨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性形象[N].中国妇女报,2002.8.203.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石孝殊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4.黄立.企服快车的母性神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
(5)
5.李淑霞.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公司注册
公司注册 
 记账报税
记账报税  税务筹划
税务筹划  一般纳税人申请
一般纳税人申请  小规模纳税人申请
小规模纳税人申请  进出口退税
进出口退税  离岸开户
离岸开户  商标注册
商标注册  专利申请
专利申请  著作权登记
著作权登记  公证认证
公证认证  电商入驻
电商入驻  网站建设
网站建设  VAT注册
VAT注册  ODI跨境投资备案
ODI跨境投资备案  许可证办理
许可证办理  体系认证
体系认证  企业信用
企业信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